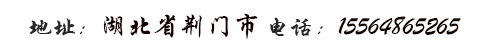诗经之兰
|
北京治疗白癜风的正规医院 https://wapjbk.39.net/yiyuanfengcai/tsyl_bjzkbdfyy/ 知北游按:《溱洧》之“蕑”,《毛传》、陆玑《疏》、《广雅·释草》、朱熹《集传》等释为“兰”,《韩诗》释“蕑,莲也”。《泽陂》中的“蕑”,《鲁诗》作“莲”,看来《韩诗》以《溱洧》之“蕑”与《泽陂》之“蕑”同,都是指莲。 第一节 春秋时期的溱洧两岸具有兰花生长的条件 诗经产生的时代大约在春秋前期和中期。笔者在本编第三章从河南北部及相应地域古代动植物遗骸出土、古代北方记兰文献和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河南北部多处有野生兰蕙的客观现实,证明了河南北部适宜兰花生长。本章具体就河南北部溱洧流域的古兰问题做个考察。 古时候的溱洧流域,就是今天河南郑州市的新密一带,地处北纬34°多一点。与之更北的近邻县市新乡、温县、焦作、济源、阳城均在北纬35°左右,新密西面的近邻嵩山(北纬34.15),更西边的陕西商洛山区(北纬34°20′)、陕西辋川山区(北纬34°)21世纪都还有野生蕙兰发表。特别是地处35°27′的山西阳城县南部山区,明代尚有兰蕙花向邑侯进贡,21世纪初也还能够看到约50平米的成片兰花,这就彻底打破了兰蕙不过黄河的说法。嵩山少林寺碑林中还有康熙二年(公元年)名画家蒋馨绘,书法家王国政题的《咏兰》诗:“托身山崖穴自闲,三经春风静闭关;谁把灵根锄出谷,幽香从此满人间。”成书于上世纪80年代的《嵩山植物志》也曾介绍过蕙兰。年7月下旬,郑州花卉协会进行了一次考察,在嵩山东麓发现了野生兰花,经对比,该兰花与少林碑刻上的蕙兰极为相似。后经有关专家鉴定,其为河南出产的“青杆蕙兰”1。历史往前推移,在我国的第二个寒冷期,东汉和六朝时代,新密南边的近邻禹州和许昌,曹操主簿繁钦写有中国文化史上第一首吟咏蕙在春末开花的诗歌,曹操的舅子卞兰写过许昌宫中春天开花的兰花。 这一切都证明新密周边古今都有兰蕙,而诗经时代,和当今气候基本一致,但水土和动植物生态环境远远优于今天的溱洧流域,有野生兰花生存是可能的。 再者,先秦记述到郑国“兰”的文献除了《诗经?溱洧》,还有《左传》直接写到郑国“兰”,“郑文公赠兰燕姞生郑穆公,并名之曰兰”的故事。在仅仅10部左右涉及植物兰的早期文献中竟然有两部文献涉及郑国兰,所以,硬要说春秋时期郑国无兰蕙,恐怕很难解释得通。 然而清代中后期的吴其濬在他的《植物名实图考》中却说“余过溱洧,秋兰被坡,紫萼杂遝,如蒙降雪”2,不见春兰飘香,绝无兰蕙踪影,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从现实植物分布看,河南北部相应地域只能够出产春天开花的兰蕙,没有秋花的物种“秋兰”。吴其濬是秋天泽兰盛花之时考察河南北部的,就算那时、那里实实在在地生长着春天开花的兰蕙,吴其濬又怎么会看得到春天的兰蕙开花呢?所以,吴其濬说他在秋天没有看见溱洧流域兰蕙开花,只见大泽兰(吴其濬认为的“秋兰”)“紫萼杂遝,如蒙绛雪”,完全合乎情理,但吴其濬的考察却不能够证明溱洧没有春花的兰蕙。当代泽兰论专家用吴其濬秋天只见泽兰开红花,不见春天类兰蕙开花来证明春秋时期溱洧流域没有兰蕙生存,这是什么逻辑呢?实在是匪夷所思。 还有一点应该引起专家和读者注意的是:清代中叶了,吴其濬还在泽兰的词条下用“秋兰”称呼“泽兰”:“余过溱洧,秋兰被坡、紫萼杂沓,如蒙绛雪,因知诗人纪实,不类赋客子虚。”吴其濬是故意混淆概念以显示学问之高深呢,还是确实清代文人都使用“秋兰”称呼泽兰呢?既然吴其濬说“诗人纪实,不类赋客子虚”,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朱熹、康熙皇帝、郑板桥、王殿森等诗人所用的“秋兰”是不是写吴其浚所考证的泽兰: ①朱熹《咏兰》 谩种秋兰四五茎,疏帘底事太关情; 可能不作凉风计,护得幽兰到晚清。 ②爱新觉罗?玄烨《秋兰》 殿前盆卉,芳兰独秀,昔人称为王者香,又以方之君子,因题四韵。 猗猗秋兰色,布叶何葱青。爱此王者香,著花秀中庭。 幽芬散缃帙,静影依疏棂。岂必九畹多,侈彼离骚经。 ③郑燮《客焦山袁梅府送兰》 秋兰一百八十箭,送与焦山石屋开。晓月敲门传简贴,烟帆昨夜过江来。 ④罗聘《秋兰文石》 今年九月偏无菊,欲纫秋菊笑可拈。画毕自看还自悔,笔花端合让江淹。 ⑤王殿森《秋兰》 闲庭习幽静,清香透书帏。起视盆中兰,娟娟开一枝。 秋光倏已晚,尔开何独迟。风声撼林薄,霜痕沾鬓丝。 孤芳孰延赏,知音安可期。我亦素心人,何时慰幽思。 ⑥静诺《咏秋兰》 长林众草入秋荒,独有幽姿逗晚香。每向风前堪寄傲,几因霜后欲留芳。 名流赏鉴还堪佩,空谷知音品自扬。一种孤怀千古在,湘江词赋奏清商。 上述诗人都使用了“秋兰”一词,但没有一首是写泽兰的。而且李时珍也只是在《本草纲目》中辩证分析时指认屈原所写“秋兰”是泽兰,但李时珍及以后的《本草经》也都没有把“泽兰”更名为“秋兰”。吴其濬怎么可以这样随心所欲的把泽兰更名为“秋兰”呢? 当然,可能吴其濬考察溱洧之时,当地的兰蕙可能已经灭绝了,但吴其濬秋天考察说没有看见春兰蕙开花的解说,不符合北方只有春花兰蕙这一生物常识,而且用“秋兰”一词称呼泽兰也与古今历史文献相违背。因此,吴其濬的考察不能够用作古溱洧流域不产兰蕙的证明。 第二,今天溱洧流域的周边,或同纬度的地域都有兰蕙发表,却没听见溱洧有兰蕙发表的信息,这是为什么呢?笔者以为:生态的恶化,不仅仅是地球寒冷期的出现,还有人为的疯狂破坏。长期的征战杀伐、反复的城邦建设,加上过度的采集,寒冷期的到来,致使溱洧这一小环境的古兰彻底灭绝,可能是很重要的因素。而蓝田辋川、山西太行深处的蟒河深林、济源的小原山因为没有溱洧那样的人为破坏,生态环境还适合兰蕙生存,所以我们今天得以在这些地方见到野生兰蕙。 溱洧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早在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生息繁衍。目前该流域已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近百处,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新砦文化遗址60多处。三皇之世的伏羲氏和五帝时的黄帝、祝融,以及西周时的密国和春秋早期郑国均先后在溱洧流域(也就是今天的新密市一带)立国建都。战国时,郑文公因交流寨(溱洧流域)一带“土狭而险”,“山居谷汲”,不适合越来越发展的郑国,就在交流寨东部二十余里的开阔地带建一新都城(今郑韩故城)。《春秋》记载说:“僖公六年(公元前年)夏,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伐郑,围新城。”《左传?僖公六年》也记载说:“诸侯伐郑,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围新密,郑所以不时城也。”由上文献记载可知,郑建都在溱洧后,就不分季节加紧筑城,因而招来以齐桓公为首的诸国的讨伐。当时诸国讨伐的目标定在新密邑,即今之大隗镇3。战国时期,郑国是处在强秦和大楚的夹缝中生存,自伏羲氏到郑国被灭,不知经历了多少征战杀伐,仅《左传》记载,“诸侯伐郑”就有12次之多。烧杀掳掠,宫室反复的修造,城邦的多次搬迁,都极大地破坏了溱洧流域的生态。因此,在气候进入寒冷期(东汉到六朝)时,兰花彻底灭绝了,即使温暖期来临,兰花再也没有恢复的条件,后世没法看到兰花也是一种可能。 第三,溱洧兰花灭绝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溱洧人因喜欢兰花而过度的采集。古溱洧人采兰赠送是不是像赠送芍药一样整株整株地采送,现在不得而知。如果不是仅仅摘花欣赏,而是像20世纪末中国人连草带花采集,加上气候环境恶化,那么溱洧古兰也会难逃灭顶之灾。举个例子,四川省名山县被中科院陈心启先生誉为“名兰之乡”,因为流入成都平原、重庆、云南、贵州、广东、香港、台湾、日本的夏兰新名品和春剑名品,不少出自名山。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里的浅丘到处是兰花,农民通常连同他草一起割来喂牛,但是,由于疯狂的兰花大潮的扫荡,年以后,名山县原来兰花成片的山坡,几乎找不到两苗连体的兰花草了。 说郑国人喜欢兰花是有根据的:在仅有的古代涉兰记述中,就有《诗经》《左传》记述到人们采摘兰花做礼物送给心上人。 因此,清代中叶吴其濬秋天不见春兰开花,只见“秋兰(泽兰,吴其濬称呼泽兰为秋兰)被坡,紫萼杂遝,如蒙绛雪”的考察结论,和我们今天在溱洧流域看不到野生兰花影踪的事实,都不能够作为春秋时期的溱洧流域不产兰花的依据。这正如我们不能够因为今天北方没有成群的野生大象,就下结论说春秋战国时期北方也没有野生大象一样。 附注: 1.少林寺碑刻王国政《咏兰》由郑州王明提供,其他介绍见《中国花卉报》特约记者兑宝峰年8月17日《郑州举办座谈会鉴定“嵩山蕙兰”》。 2.(清)吴其濬著,《植物名实图考校释》页,中医古籍出版社,年1月。 3.新密市档案局《新密市档案信息网》年10月28日。 第二节 郑国青年男女手持兰花做礼物更合乎情理 第一,兰花是可以秉持作赠礼的植物。 先秦因为兰花馨香独特,被誉为“国香”,是“养鼻”佳品,所以在传世不多的先秦记述里,确有几种文献记述到古兰是作为赠品的植物。《左传》记载的是郑文公梦见天使送兰花给自己。后来郑文公也就用兰花作为求爱的信物赠送给燕姞,生下了郑穆公,这是诸侯王把兰花送给心上人的例子。郑国稷下学宫整理的《管子》第一次提到“春献兰”“祭尧之五吏”,祭品实际上也是礼品,是活着的人向神灵或祖宗灵魂敬献的礼物。此外《礼记?内则》记载说:“妇或赐之饮食、衣服、布帛、佩帨、茝兰,则受而献诸(之于)舅姑。”《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但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名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先秦的其它典籍,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仪,解释仪礼,记述修身作人的准则的先秦文献,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因此,《礼记》记述了“妇”接受他人馈赠的礼品饮食、衣服、布帛、佩帨和“兰蕙”,还应该把这些礼品献给自己的长辈(舅姑)的礼制。请注意,这里的“茝兰”就是“芝兰”,是和“饮食”“衣服”“布帛”“佩帨”四类礼物并列的礼品,可见兰不是一般的泽兰,因为与泽兰一样的植物太多了,而且“如梦绛雪”到处都是,怎么可能拿来作和“饮食”“衣服”“布帛”“佩帨”同等的并列礼品呢!汉代到唐代中叶,诗文中写到摘兰花、赠兰花、佩戴兰花的文字不少。仅笔者所见,汉代至隋代言采兰的31见,唐代的49见,其中明确写到采兰之花的10见。赠兰的记述,汉唐一共有15见。晚唐唐彦谦《寄同上人》也写到兰花做贡品的内容:“云藏三伏热,水散百溪津。曾乞兰花供,无书又过春。”这些文献资料证明以兰花作赠礼是有风俗继承性的,而从古到今却没有见到赠送泽兰和佩戴泽兰的任何记述,这是不是应该引起考证者深思呢! 第二,手持兰花作礼品求爱比手持很快萎蔫的泽兰嫩苗更合情理。 夏历二月,溱洧河畔的山野已经有兰花开放了(蕙兰就可能只有花骨朵),郑国青年男女挑选自己喜欢的兰花捆扎成束或整丛含着花骨朵的蕙兰草,遇上心爱的人,就像郑庄公送兰花给燕姞一样,送给他(她)作为友好的信物,大致类似于今天送红玫瑰吧。彼此有意,一起游玩(《溱洧》中“观”字的正确解释是“游玩”),一起聊天,高兴了,也许就在这部落“奔者不禁”的日子里,在青青的草地上成其百年之好,结为夫妻。 兰花可不可以用手秉持,并且能够维持多长时间呢?笔者亲自试验,农历六月,早上摘取建兰花箭和木本嫩枝(笔者这里没有泽兰)进行对比试验,一小时后,木本嫩枝已无生机,兰花6个小时后,还很有神韵,12个小时后,兰花花箭还可以观赏,也有馨香,可见秉兰花可以作为男女相爱的礼物。其实,今天人们送礼的很多花卉都是“质弱易萎”如兰花的,比如红玫瑰、黄角兰、郁金香之类都是人们喜欢的花卉,这都能够证明兰花可以作为礼物送给心上人。 那么,我们再来分析泽兰论认为郑国青年男女手持的是泽兰的说法成立与否。“招魂续魄,拂除不祥”的鬼话,已经被人们抛弃了,单说这手持泽兰嫩苗是个什么光景吧。如果所秉(执)的是泽兰嫩苗,那是什么神态?试想,哪个青年男女会恭恭敬敬地手持垂头耷耳的泽兰的嫩尖去会友或求爱?假如是在河边马上掐几枝泽兰嫩尖,按照李时珍的分析揉一揉,湿漉漉的,蔫头耷脑的给对方佩上,让对方只能够勉强闻到一点普通草本植物的清香,这能够和有神、有韵、有幽香的兰花比美吗?这样漫山遍野、唾手可得的贱生物作为求爱的礼物,是不是也太廉价,太没有情调了!而兰花的花朵带茎摘下扎成束,比今天的黄角兰还漂亮,即使摘下的兰花在春阳之下半天,幽香依旧,花朵也不会萎蔫得不成样子,而且其神态也远胜于比兰花花朵蔫得更快的泽兰的嫩苗。所以笔者以为,果真手持萎蔫的泽兰嫩苗招魂或求爱:则招魂,魂不归来;求爱,爱不应答。 再者,生长在山野的大泽兰叫佩兰,《本草乘雅》载:(佩兰,泽兰的同属)“臭香,味辛,气化中药也。”现代医学告诉我们:“佩兰能引起牛羊慢性中毒,侵害肾、肝而生糖尿病。鲜叶或干叶的醇浸出物含有一种有毒成分,具有急性毒性,家兔给药后,能使其麻醉,甚至抑制呼吸,使心率减慢,体温下降,血糖过多及引起糖尿诸症。”1古人虽然没有今天的医学知识,但是生活的实践会告诉他们佩兰是不是他们谈情说爱所需要的香草。 由于古兰与今兰的争论的深入,泽兰论也感到纯粹的秉兰“招魂续魄,祓除不祥”之论不能够自圆其说,于是就把招魂续魄与男欢女爱糅合在一起修正泽兰论: “春秋时的郑国于“三月上巳”有“执兰招魂续魄,祓除不祥”的习俗,地点在都城新郑的溱水洧水边,举行盛大的除邪求福(祓)的祭祀。青年男女并借以谈情说爱或“行夫妇之事”。希望通过人的性行为让正在孕穗的小麦丰茂。这是把“兰”作为生殖灵物的巫术行为,是残存的母系制婚姻的遗风。为什么看中“兰”呢?原因有二,其一,兰(佩兰)的生殖器官“花”为“头状花序”,作药用可调治妇女月经,其暗示的生育原理是不言而喻的。”2 泽兰论专家的想象力都很丰富,汉代薛汉从短短的几句诗就读出了《溱洧》是写上巳节盛大的水边招魂续魄祓除不详的盛况;当今的专家也能够考证出郑国青年男女手持泽兰祓除的原因:因为“兰(佩兰)的生殖器官“花”为“头状花序”,“作药用可调治妇女月经,暗示的生育原理”,郑国青年男女就因此借“性行为让正在孕穗的小麦丰茂”。 不过,笔者实在不知道泽兰对于中华民族之祖先如此重要,但遗憾的是把《诗经?溱洧》以及先秦现在可见的全部文献的每一个字都拆开来研究,也看不出泽兰曾经有如此强大之功能。泽兰论专家这样的论据远胜于陆玑、李时珍的创造,让古代考据家都望尘莫及了。不过,仅凭泽兰论专家的这种推断,不见文献依据,叫我们怎么相信这是真理呢?! 有趣的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本草》编委会编著的《中华本草》,其佩兰(即大泽兰)“药理作用4”说:服佩兰能引起小鼠动情周斯暂停,排卵受到抑制。那么,我们是不是要分析出郑国青年男女用大泽兰求爱,有避孕的意图呢?假如郑国青年男女那时就已经朦胧地知道用大泽兰避孕,这样一分析,那就真不敢想泽兰论还能够分析出什么结论来了! 关于诗中郑国青年男女见面送古兰,分手送芍药,也是争论激烈的内容。 笔者以为:既然泽兰论专家认为嫩嫩的泽兰苗都可互赠,为什么芍药就必须带花呢?这是不是在把民歌当着科技说明文在读呢? 《溱洧》不是调查报告,是民歌,诗中的一些内容在于渲染气氛,诗中只写到送兰和芍药,未必实际的场景中每对青年男女都只能够送兰和芍药,那么同理,是不是每对青年男女都是开头送兰,最后送芍药呢?《诗经》记载卫国风俗还有男女青年赠送木瓜、木桃、木李求爱的。《诗经?静女》中还描绘说,静女送男友的礼物是“彤管(红色的茅草,一说红色的管箫)”,为什么郑国男女就只能够送泽兰嫩苗和芍药鲜花呢?除非这是专门导演的集体婚礼才可能如此的规范和机械:见面送什么,分手送什么;然而实际的生活绝不可能是这样! 有专家提出质疑:那么多青年男女在一起,溱洧两岸有那么多兰花一人一束吗?他们认为据清代吴其濬实地考察,溱洧两岸漫山遍野都是大泽兰,只有大泽兰才能够满足成千上万的青年男女采集赠送,因此诗经《溱洧》中的兰就只能够是大泽兰嫩苗。这种推理面对的是实际社会生活调查,那还是有理的,然而,这是写诗啊,谁统计过真有成千上万的青年男女在一起呢?何况就是一万对青年男女一起,也不一定要人人都手持兰花啊;有几十、几百对青年手秉兰花,也就是洋洋大观了!诗就可以这样写了!谁见过写诗是要一一去数,是不是人人都手秉兰花才能够写“方秉蕑兮”呢?何况求爱者不一定人人都要持兰花,诗中的青年不是还有送芍药的吗?泽兰论专家不是说这些青年男女送的是泽兰嫩苗吗?既然泽兰嫩苗都可以赠送,为什么不能够赠送其他花卉呢?正是机械理解该诗,才把一首青年男女求爱的诗讲得面目全非。所以研究诗歌中气氛的渲染、象征比方之类绝不能够同研究科技论文一样。 其实,郑国青年男女见面送兰之鲜花,临别赠送带块茎的芍药(已经出苗或只有芽的块茎都可以),希望对方带回去养殖亦未可知。何况古代的人们有借赠芍药表示恩情,缔结良约的意思,并不一定要送芍药之花才能够表达“如约”的意思。钱玉趾考证说:“赠之以勺药”,在古诗词中,“药”读作yuè,与“约”同音。“勺药”的谐音是“勺约”,有获得盟约的意思。《溱洧》中相恋的男女,一方赠送芍药,—方接受芍药,意味着已经进入了情投意合、心心相印,甚至海誓山盟的境界了。在美妙的季节,在美妙的地方,以手执香兰开头,以赠芍药结尾,《溱洧》写得是多么美妙、精湛而蕴藉!”3 第三,春秋时代,溱洧流域的二月,如果有野生春兰,那正是开花时节;如果只有芭茅兰一类的蕙兰,那也有带花苞的草丛。古郑国如果有春兰,则青年男女彼此送兰花合情合理。如果只有芭茅兰一类的蕙兰,则所送的蕙兰草也如诗中所说的送“芍药苗”一样,是符合生活实际的;因为部落允许男女求婚的时间是固定的农闲二月,彼此有意的青年男女也就只能够送还没有开花,但开花后十分美好的植物了:总之,能够代表美好祝愿,能够表达真情就可以。 综上所述,《郑风?溱洧》所写的是仲春时节男女欢娱求爱的场面,在古代可能产兰的溱与洧二水山野,青年男女所持的古兰(“菅”或“蕑”),应该是今天的兰蕙鲜花或兰蕙草丛。 退一万步说,即使《诗经?溱洧》所记之兰,确实不是真正的兰花,是古人误把茅草“菅”同《左传》《列子》所记之“兰”弄混了,那也仅仅《诗经》这一例不是记录古人使用兰花记载,但是也无法否定历史上那么多明明白白显示着兰科植物属性的言兰记述,也无法否定21世纪比溱洧流域更北面出产兰蕙的客观实际。先秦丰富的言兰记述才是那个时代兰花是什么植物的最好证明,我们考证绝不能够舍本逐末! 附注: 1.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编,《中华本草》“佩兰?药理作用”,上海科技出版社年1月。 2.《黔西南日报》新闻网《中国黔西南》文化讲坛:年11月7日第十讲《“兰文化”说略》。 3.钱玉趾《〈诗经?溱洧〉的主旨及其他》,见《文史杂志》年01期。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合集#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zelane.com/zlyy/14305.html
- 上一篇文章: 方剂习读麻黄汤
- 下一篇文章: 一键ldquo云赏rdquo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