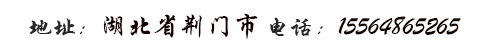当代生物污染肆虐的文化成因探析
|
当代生物污染肆虐的文化成因探析 杨庭硕,杨 成 (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湖南吉首 ) 摘 要:20世纪末,生物污染猖獗,已经构成了生态灾变的一个主要方面,严重地危及到了相关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并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物污染、外来物种入侵频繁见诸于生态学研究的相关论著中。有关报道指出,生物污染已经给相关地区和相关民族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成了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之一,生物污染已经成为当代生态灾变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对当代生物污染肆虐成因的探讨,学术界却其说不一。代表性的结论可以大至分为三类:一是,认为生物污染肆虐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现象,对付的办法只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淹”,针对性地采取工程技术措施;二是,认为当代生物污染肆虐是现代化的伴生产物。人类要追求现代化,就必然要对此付出代价。解决的办法只能寄希望于新的科学技术发明去加以解决;三是,认为生物污染猖獗是人们认识不足,行为不审慎而造成的恶果,解决的办法只能通过立法或教育的手段,提高人们的认识去加以解决。上述各种观点,在具体的生物污染问题上,都能言之成理,对治理生物污染也能发挥明显的作用,但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当今社会上的任何个人都有其特定的民族文化归属,不同民族的个人其生态行为及生态后果,都会呈现出规律性的差异,生物污染在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会呈现出不同的差异。因而,探析当代生物污染猖獗的成因,有必要引入民族文化这一要素,才能全面地澄清当代生物污染的成灾机制,并找到更经济有效的防治对策。 在纯粹的自然背景下,不同地区的生态系统在长期的历史沉淀中都会形成稳定的生物制衡格局,能有效地抵御外来物种的入侵,因而发生生物污染的情况极为罕见。与此相应,并存各民族间靠各民族建构的不同文化去维系人类社会的运行,并存文化之间也构成了另一种形态的制衡,那就是文化制衡。在文化制衡机制的作用下,不同民族的资源利用方式互有区别,因而引发生物污染的途径和方式也会各不相同。生物制衡与文化制衡,从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就一直长期稳定并存,并在一定程度内对生物制衡构成冲击和干扰,同时给生物污染的途径和方式赋予了一系列新的内容。这种状况一直延伸到当代,并派生出了一系列新的特点和状况,共同导致了当代生物污染的猖獗。为此,我们认为,在探讨当代生物污染肆虐的原因时,决不应当忽略民族文化这一要素。正是当代民族文化制衡的新特点,给人类社会种下了生物污染肆虐的祸根。要有效地改变这一局势,也必须从民族文化制衡格局这一原因入手。 二、生态系统的四道防线 人们能观察到的生态系统,不仅是客观的存在,同时也是长期历史积淀的产物。在一个特定的生态系统中,包容进什么样的生物物种,各物种的种群规模有多大,都会以生物体对外界物质能量的截获和信息的利用为转移。各生物物种通过长期地磨合结成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这就是生物制衡。生物制衡格局的稳态延续,也就确保了该生态系统的稳定存在。一切能稳定存在的生态系统都可以通过四道防线有效地遏制外来生物物种的入侵,所谓生物污染也就会变得极为罕见。 生态系统的第一道防线是空间和时间的阻隔。靠生物遗传机制稳定下来的不同生物物种,其空间移动与生命周期的延续都是一个稳定的常数。生物体在通常情况下很难逾越大自然已有的阻隔,即使空间移位最强的候鸟,它的迁徙路线也是稳定的,不会毫无规律的在地球上漫游。至于其它动物,个体能够逾越的自然障碍就更其有限了。相比之下,植物的传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自己不能做主,物种的传播往往得借助自然力或动物携带,因而逾越自然障碍的能力更其有限。这样一来,处于特定区位的不同生态系统,外来物种进入的可能性本身就很小。因而这些生态系统在自然状况下,能较好地免受外来物种的入侵。 生态系统的第二道防线,是生物制衡格局的稳态延续。每个生态系统的生物制衡格局一旦达成稳态延续,该生态系统中的各生物物种之间,都会围绕着物质与能量的截获和信息的利用在该地区形成一个均衡的格局。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后,能利用的空间、物质、能量和信息都会趋于饱和,也就是所有生态位都被挤占一空。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外来物种要找到立足的生存空间就会极其艰难。即使勉强存活下来,其生命延续和繁衍也会受到其它生物物种的制约,不可能扩大其种群。因而,各生态系统生物制衡格局的定型,能有效地抵御外来物种的入侵。例外的情况,仅出现在并存生态系统之间的过渡地带。在这样的过渡地带,由于受自然本底特征的制约,相邻各生态系统的生物构成物种虽说可以勉强在这样的过渡带存活,但生命力和繁殖力都要受到限制。因而会留下有限的可供利用的生存空间。在自然状况下,外来物种要获得存活,往往只能着生在这样的过渡带上,并且还必须经过漫长的适应过程,才能勉强的存活,要扩大成灾变,需要的适应时间也就更加漫长。由于这样的过渡地带范围小,而且自然背景不稳定,顺利存活和扩大种群的难度也很大,因而即使勉强存活也不会发展为严重的生物污染。可见,在纯自然状况下,第二道防线比第一道防线更具能动性,能够能动地清除偶然进入的外来物种。 生态系统的第三道防线,是不同生物靠自然选择而磨塑出来的适应能力。在自然状况下,每一个生物物种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后,都会高度特化,针对性的适应于某一个特定的自然背景。每个物种进入一个新的自然环境后,其适应能力都会明显地下降。因而,外来物种即令在并存生态系统的过渡带免强存活下来,由于所面对的自然环境和它的原生地不同,以至于其生命力和繁殖能力都会明显地下降。如果它要获得在新地区的适应能力,又得经过漫长的自然选择的磨塑。这道防线的存在,致使偶然存活的外来物种,也不容易顺利地扩大其种群,从而起到了防治生物污染的作用。 生态系统的第四道防线,来源于各生物物种特有的免疫能力。任何一个生物物种要顺利存活,都必须抵御各种微生物的入侵,并在遗传机制的长期作用下形成自己的免疫能力,去应对微生物的入侵。生物体获得免疫能力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对没有接触过的微生物就不可能获得有效的免疫力。这样一来,偶然进入一个新生态系统的外来物种,一般都难以渡过当地特有微生物感染的难关。致使该生态系统固有的生物物种会表现出更强的生命力,而外来物种则会经常染病。缺乏免疫力这就在客观上发挥着抑止外来物种入侵的作用。 正是凭借上述四道防线,在纯粹的自然生态环境下,外来物种入侵的实例并不多见,引发为生物污染的可能性更其鲜少。但介入了人类社会存在这一要素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一方面,人类能在一定限度内能动地改变自然面貌,当然也改变了生态系统的结构。另一方面,人类的活动能力比任何生物物种都强,这会给生物物种的传播创造更多的机会。再一方面,人类还可以通过医药手段,使外来物种逃过微生物的攻击。最后,人类还能够为外来物种建构一个有限的人文环境,避免外来物种因不适应而灭绝。人类在这四个方面的能动性,都会在不同文化的规约下,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表现形式虽不同,但结果却一致,都会在有意、无意中推动生物污染的肆虐。 三、当代文化与生物制衡的失灵 进入20世纪后,随着廉价石化能源的开发利用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跨文化和跨地区的人流和物流随之加快,流动的规模也飞速上涨。频繁的物流不仅可以把外来物种直接带到了世界各地,还会在无意中夹带进外来生物物种。规模巨大的人流也会在无意中将外来物种带到世界各地。这样一来,生态系统防止外来物种入侵的第一道防线,在人类社会中被摧毁。今天世界各地生物污染的肆虐显然不是纯粹的自然现象,而是当代民族文化推波助澜的直接产物。水浮莲、紫茎泽兰、德国蟑螂近年在中国肆虐,从终极意义上讲,都是中外物流、人流飞速扩大的派生结果。恰好是当代文化的运行方式帮助外来物种突破空间的阻隔和时限的制约,使这些外来物种在中国大地上生息繁衍,泛滥成灾。 和生物制衡一样,文化制衡也要受到空间和时间阻隔的限制。在历史上,世界上并存的各民族都习惯于集中消费当地所产的生物制品,对外来物种虽然充满了好奇,但要引种却需要克服时间和空间的障碍。因而外来物种流入的数量和规模都极为有限,加上技术装备的不足,外来物种要迅速地扩大种群规模也极为困难。这就有利于文化制衡格局的稳定。而文化制衡格局的稳定又反过来维护了生态系统第一道防线的持续生效。然而,在当代社会,由于能源的价廉和技术装备的先进,在突破文化制衡格局的同时,也侵蚀了生物制衡的自我调节能力。在有意、无意当中帮助外来物种突破时空的限制,传播到世界各地,对于生物污染的肆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不是直接利用纯自然的生态系统,而是要凭借自己特有的民族文化去对客观的自然生态系统进行有计划的加工和改造,从而形成了兼具自然和文化特色的特殊生态系统,这就是各民族的民族生境。民族生境的存在完全是服务于相关民族利用的需要,因而它必然打乱自然生态系统的制衡格局,使并存物种间的依存制约关系松弛。这就在无意中为外来物种的着生,打开了方便之门。另一方面,在民族生境中人类还可以根据本民族文化的需要,有效地控制和改造空间布局,从而留下较多的空缺生态位。上述两种作用的共同后果就会使得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境,都会像并存生态系统之间的过渡带那样,成为外来物种的理想着生地。随着一个民族的发展和民族生境的扩大,在自然环境中,范围极其有限的过渡带会变得越来越宽阔,于是就成了外来物种顺利渡过适应难关的温床。这样一来,生物制衡这道防线也在无意中被民族文化所摧毁。 随着科学装备的健全和完善,当今世界各民族控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都得到了迅猛的提高。这就意味着,各民族对所处自然生态系统的改造更其深化,而改造的结果就直接体现为空缺生态位的扩大。在现代化的都市中,高大建筑之间的空地往往会成为生物入侵的理想着生点。现代居室条件的改善,会使室内成为外来昆虫越冬的避风港。现代的塑料大棚种植,虽说可以提高农产品的产量,但同样可以使外来物种免受生物制衡的规约,而得到种群的迅速扩大。总之,现代技术装备在推动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却在无意中摧毁了生物制衡这道防治生物污染的防线,使原先在自然状况下不能构成生物污染的外来物种,也能在当代社会条件下泛滥成灾。 民族生境总是特定民族文化规约下的产物,因而各民族的生境都有其特异性。这就导致在历史上,各民族的资源利用模式各不相同。以至于并存各民族间对生物资源的消费能够长期保持均衡状态,不容易出现资源的单向倾斜消费。当代社会则不同,随着各民族视野的扩大,助长了人类好奇心和虚荣心的膨胀,追求时尚被导入了民族生境的建构中,这会打乱原有的文化制衡格局。当今世界上,不管是哪个民族都在追求时尚,都在有意无意地引进外来生物物种,同时还夹带进有害的伴生生物物种,从而导致各民族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生物制衡的失灵。这种有意识地摧毁生物制衡格局更其有害。中国为了追求时尚,在引进啤酒酿造的同时,出于经济的考虑,又连带着要引种大麦和啤酒花。这种有意识地引进外来物种,由于是生活在民族生境之中,而不是生活在纯粹的自然生态系统中,摆脱了生物制衡的控制,因而在人类的羽翼下发展成有害的生物污染。近年来,我国在引进国外鲜果的同时,也在无意中夹带进了国外的果蔬病菌和害虫,不仅损害了引进品种的质量,还连带着损害了我国原有品种的质量。从这一意义上说,当代民族文化中正在泛滥的时尚追求和对异种文化的好奇,已经严重地摧残了原有的生物制衡格局,为生物污染的肆虐大开了方便之门。 各民族文化能使人类获得超越于任何生物物种的能动性和创造力,这样的能动性和创造力不仅使人类追求舒适的愿望得以满足,同时也在无意中帮助有害的外来生物物种渡过适应能力下降的难关。很多外来物种,并不适应于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比如,从澳洲引进的桉树,引种的初衷是作为重要的经济作物加以推广。但澳洲的多种桉树并不适应于我国西南地区的气候环境,一次中等强度的寒潮就可以将连片的桉树冻死。也就是说,按照自然规律,桉树绝不会对中国的西南山区构成生物污染。然而,事情却恰好相反,我国的科技工作者从温室培育、抗寒能力培育、树种搭配各种技术手段都用尽了,最终才使桉树在我国的云南、广西,贵州连片成林。但结果却富于讽刺意味。桉树一旦成林,由于它的需水量超过了我国西南山区的极限,这就直接造成了我国原有的生物物种被桉树林吞食,严重的地带甚至乡民的饮用井水和泉水都为之枯竭。构成了我国西南山区严重的生物污染灾变。最后不得不全民动员砍伐桉树。并连根挖出树根。在这个实例中,桉树并不具备在我国顺利成长的适应能力,恰好是人类自己帮助桉树提高了适应能力,从而摧毁了生态系统的第三道防线。除了桉树外,西双版纳和广西南部连片种植的橡胶林也正在酿成新一轮的生物污染灾变。 文化制衡的作用之一,就是要规约不同民族的生态行为,而稳定的生态行为对生物制衡的冲击也就得到了相对的稳定,外来生物物种的可乘之机也因此而得到了有效地控制。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受到了市场价格波动的驱使,各民族传统的生物资源利用模式也会受到严重地干扰。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很多民族都会很自然地竟相引进外来物种,并且投入巨大的科研力量,帮助这些物种提高其在新环境的适应能力。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总会表现的有利可图,但从长远的生态效益看却是在给经济的发展挖掘陷阱。近年来,欧洲蒲公英在日本泛滥成灾,而这种蒲公英在自然状况下,原先并不能在日本顺利的成活。日本人是出于好奇,开始是作为观赏植物引种,后来又作为蔬菜使用。但却没有预料到,这种蒲公英一旦渡过了适应性下降的难关后竟成了吞食日本本土蒲公英的魔王。它的花粉可以抑止日本蒲公英的授粉,使日本本土的蒲公英不能顺利的繁衍后代,终于酿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生物污染。如果不是人为的干预,欧洲蒲公英显然不会在日本泛滥成灾。传统文化制衡格局的松弛,在这个实例中正是一个关键性的导因。追求时尚新奇,对传统文化的侵蚀不仅是一个观念性的扭曲,更是生物污染灾变的开路先锋。 现代科技手段有效地维护了人类自身的健康,但这种技术在文化歧变的背景下,也会滥用于外来的生物物种。这就会使得生态系统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第四道防线彻底崩溃。 人类为了追求居室环境的舒适,为了农作物的高产可以使用化学农药清除有害的昆虫,从短期效益看十分理想。但这些化学毒物并不长眼睛,在杀死各种有害昆虫的同时,也将这些害虫的天敌一并杀死。这就使外来物种的进入可以免受天敌的制约。人类发明的医药除了给人医病外,也会用于给外来物种治病。这些医药在控制有害微生物泛滥的同时,也会使外来物种获得一个保护伞,可以免受微生物的侵袭,以至于没有稳定免疫力的外来物种也会在世界各地种群失控,酿成严重的生物污染灾变。中国近年来不少严重的生物污染灾变都一再表明,这些外来物种在中国很少遇到病虫害的威胁。而这正是我们在滥用医药成果的同时,始料未及的后果。一个不该忽略的严重问题在于,由于我国的农田大多超量使用化肥和农药,以至于弄得在农田中,除了庄稼之外寸草难生。从短期的经济效益看似乎很有利,但在农田中却出现了极大的空缺生态位,在这样的空缺生态位中,微生物也不能成活,严重的损害了微生物对外来物种的控制力。这将会给外来杂草、害虫入侵中国农田铺平了道路。中国西南三省紫茎泽兰的泛滥,在一定程度上与农药和化肥滥用存在着关联性。 从表面上看,生物污染肆虐是生态系统四道防线失灵导致的直接后果,但深层意义而言,则是民族文化制衡格局在当代振荡的伴生产物。当代生物污染的肆虐绝不是纯粹的自然现象,因而也不能用单纯的技术手段去加以对付,只有从当代文化制衡格局振荡入手,才能找到有效控制生物污染灾变的文化对策。 四、防治生物污染的文化对化对策 面对生物污染的肆虐,不同学科的专家纷纷推出各式各样的对策。工程技术人员推出的对策,大多趋向于利用单一的工程技术手段,针对性地清除已经成灾的外来物种。鉴于上文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自然界,生态系统抑止外来生物物种入侵是凭借四重防线构成了一套立体的防护网络,因而能有效地抑制生物污染。而技术手段防治生物污染,由于手段过于单一,因而很难挡住无孔不入的外来物种入侵。更其严重的还在于,过分单一的对策在清除污染物种的同时,还在无意中损害了当地自然生态系统的自然防线,反而会给新一轮的外来物种入侵大开方便之门。以至于防治生物污染成了一个没完没了的拉锯战,旧的生物污染得到抑止,新的 生物污染又接踵而来。社会科学工作者则过分地依重经济、法律和教育手段,遗憾的是,经济、法律和教育手段可以规约人的行为或提高人的认识,这对于有意识行为诱发的生物污染当然能发挥明显的抑制作用。但问题在于,人类的经济、法律和教育制约不了生物物种,因而人类活动无意识导致的外来物种入侵,上述各种社会手段几乎是无能为力。边境上的执法检查再严格,绝对控制不了人员和货物夹带进来的外来物种。因为,外来物种入侵的渠道隐蔽的一般性的执法检查手段都无从察觉。何况进行这样的执法检查,其执法成本极为高昂。即令发现了线索,要用人为手段阻断外来物种的入侵渠道都得耗费高昂的代价。这乃是我国的执法日趋完备,但外来物种的入侵却禁 而不绝的原因之所在。通过上文的分析不难看出,生态系统之间的过渡带往往是生物入侵的脆弱环节。与此同时,文化分布的交错地带也会成为外来物种入侵的滩头阵地。如果这两种交错带相互重合,就会成为生物污染的策源地。因为在这样的地带,生物制衡不能有效地发挥防治作用,文化制衡也会脱控。如果能够将这样的敏感地带纳入文化运行的轨道,一方面,激活当地固有生物制衡机制,使这样的地带形成稳定的生物群落,靠生态系统自身的制约力去为人类控制生物污染。另一方面,将文化的制衡延伸到这样的交错地带去。通过利用方式的改变,使入侵的外来物种无法泛滥成灾。整个防治对策,都围绕着激活文化制衡格局,通过扶植生物制衡机制去实现对外来物种入侵的立体网络式防范。这就是我们所 主张的文化防治对策。文化对策的核心正在于对民族文化实施诱导重构,从而引导资源利用方式的改变,以此激活生物制衡机制,凭借生物制衡的固有防治能力替人类消除生物污染灾变。这种对策的优势在于,不需要动用特殊的技术手段,也不需追加防治成本,就可以持续地发挥防治生物污染的功效。紫茎泽兰污染在我国西南三省已经成灾,为了清除紫茎泽兰已经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收效甚微。贵州省镇宁县南部的六马山区,是优质六马桐油的生产基地。当地布依族林农,为获得桐油的高产和稳产习惯于在桐树林中精心地清除一切杂草,特别是在桐籽收获前的最后一次除草,耕作极为精细。但这一传统的操作,恰好给紫茎泽兰的漫延创造了可趁之机。季节性的林间生态位空缺,会使得这片桐油基地陷入了紫茎泽兰漫延的困境。如果稍微改变一下耕作方式,在林间引入当地生命力旺盛、有一定经济价值,而植株较高的草本植物,避免在林间形成季节性的空缺生态位,新形成的次生生物群落自身就可以抑制飞机草的漫延。引入的物种还能够产生一定的经济收入。这样的文化对策比起劳神费力去清除紫茎泽兰,不仅有效的多,而且省时省力的多。 类似的作法在云南也有一些少数民族正在试用。在云南,当地各族居民鉴于紫茎泽兰在农田中的泛滥,并没像传统的作法那样去人工的清除紫茎泽兰,而是将旱地改成了牧场,或者完全轮休,凭借当地丰富的本地生物资源形成严密的次生植被去抑止紫茎泽兰的漫延。他们能这样做,是因为当地的彝族,白族都有农牧兼营的生态传统。只要能及时地发现这一有利的文化因素,并及时地加以利用,对付紫茎泽兰的漫延不仅成本低廉,而且还可能推动产业的转型。文化的诱导重构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发挥意想不到的生物污染防治作用。 水浮莲对我国三大淡水湖的水体污染,也是久治不愈的生物污染顽症。时至今日,普遍采用的办法仍然是采用人工的办法,直接清除水浮莲。生物学家企图引进专门吞食水浮莲的蚂蚁,去对付水浮莲泛滥。但却可能诱发新一轮的生物入侵,潜在风险极大。如果采用文化对策,最好是将水浮莲纳入可供利用的渠道,将污染物转化为资源,在利用中靠文化运行的力量去控制水浮莲的漫延。举例说,将水浮莲加工成饲料,在当代中国并没有技术难度。生产成本高,完全可以通过环境投资的方式加以补贴。只要一经纳入可利用资源的渠道,水浮莲就不可能泛滥成灾。因为人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担当起天敌的角色,在文化的规约下,对污染生物构成可持续的制约力。也可以换另一种方法,直接将水浮莲作为沼气生产的原料使用,从沼气发酵的废液中回收肥料施用于农田,这样做不仅可以回收能源、肥料,还可以有效地控制水浮莲和其它水生杂草的泛滥。 在上述实例中,生物污染的策源地都处于自然生态系统和民族文化直接利用系统之间的交错带。对付生物污染的文化对策,就是得把好这样的交错带。不能容许在这样的交错带出现文化控制和生态位的空缺。这两项空缺的存在,意味着生态系统四道防线的缺失。文化对策的目标就是要在这些空缺位置,通过文化运行的力量培育新的具有本地特色的生物群落,靠生物自身的防治力对外来物种的入侵实施立体防范,或者通过文化的力量将人类的活动纳入当地的生物循环中,使人类的正常生活可以充当污染生物的天敌,在利用的过程中清除生物污染。 生物污染的文化对策,是一个综合性的防治理念。它反对使用单一的手段,不管是技术的,还是社会的去对付泛滥成灾的生物污染,主张靠文化的正常运行,靠资源利用方式的转型去激活和修复所处生态系统的自我防卫机制。最大限度地借助自然力,去控制外来物种的入侵。对已经成灾的生物污染,则希望通过利用方式的转变,将污染物种转化为可以利用的生物资源,从而实现成本最低化的生物污染防治,同时尽可能降低防治生物污染所伴生的负作用。特别是滥用化学药剂,滥用广普抗菌素所导致的副作用。由于生物污染的文化对策目前还仅是一个新的理念,不完备之处在所难免,付诸实践应用的操作程序也有待进一步规范。但只要研究的取向转移到这方面来,通过不同学科学人的努力,生态人类学提出的文化防治对策,最终肯定可以在未来的生物污染防治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原文刊登在《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2期 杨庭硕,杨 成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caodoukou.com/zlyy/5574.html
- 上一篇文章: 川芎泽泻朱砂天竺黄泽兰地锦草
- 下一篇文章: 农村这种野草叫破坏草,农民都不喜欢,可